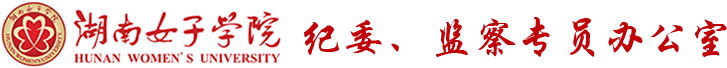父亲虽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却从不重男轻女,生活中似乎更偏爱女儿。小时候我们全家上下八口人,生活多少有些窘迫艰难。左邻右舍见妈妈宁肯委屈自己也要咬牙坚持送我们上学,便时常劝妈妈:“儿子上高中也就算了,女儿还读什么初高中呢?反正要嫁出去的。”不善言谈的母亲回家转告父亲,父亲不悦:“儿女都一样,只要她们会读书,即使砸锅卖铁,我也要供她们上学。儿子的人生代替不了女儿的人生。”父亲常用激将法鞭策我和姐姐:“不要以为你哥考上大学,对你们今后有什么好处。在我的一统之下,还有兄弟姐妹的情份,今后各自成家,谁还顾得了谁?路是靠自己走出来的。自己不努力,谁也帮不了你。”
初中时,学校离家较远,每天要快走一个小时才能到学校。那时家里没有闹钟,每天鸡叫三遍,母亲会准时叫我起床,只要东方一发赤,父亲便催我:“小丫头,天快亮了,赶快走。”我们俩一前一后迈出家门,听任沙沙作响的山风在耳边肆虐。万籁俱寂的夜晚,“山风吹空林,飒飒如有人”的空寂山野多少让人有些不寒而栗。在无数个月黑风高孤寂冷清的夜晚,在无数个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日子,父亲就这样坚持不懈地陪我行走在那寂寥清幽却又绵延悠长的山村小路上……
父亲酷爱读书,因家中贫困早早便辍学了。但勤学好问记忆超群的父亲,硬是凭着只读过半学期蒙书的底子,阅读了不少古典书籍。父亲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常常太阳还有丈把高,他便停下手中所有的农活,一手拎着小方桌,一手提着热水壶来到阶沿上,然后泡上浓浓的粗叶子茶,点上大叶子烟,戴上老花镜坐下来,津津有味地翻看起《三国志》来。遇到不认识的字,他会高声大叫:“小丫头,快过来,这个字怎么读?”这时我会飞奔上前告诉他,只要教他一遍他就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四年级时我得了重感冒又后转为伤寒,父母就轮流背我上下学。有次父亲背我回家途中问我:“小丫头,你们教室黑板上画有黄河中下游流经的五省二市图,你记得是哪五省二市吗?父亲见我哽哽咽咽半天仍说不全,立马脱口而出给我补充。至今的我仍仰慕他过目不忘的好记性,更钦佩他处处留心皆学问的态度。
也许父亲心中永远藏着一个读书梦,只是圆梦的不是他而是我们而已。我们五兄妹中除了大哥因“文革”没机会上大学外,其余四人均上了大学,二哥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姐姐是村里迄今为止唯一的硕士研究生。在我们那个村,可谓是前无古人,在少子化的今天,亦很有可能是后无来者。虽说我们五兄妹都过着普通人最为平凡的生活,从事医生和教师最为普通的职业,没有大富大贵,但这足以让生不逢时饱受失学之苦的父亲聊以自慰引以为豪了。
能说会道的父亲在村里享有较高的威望。邻里间婆媳纠纷或是夫妻矛盾,有时也会请父亲前去调解。每次调解完婆媳矛盾回家,父亲对我和姐姐总是语重心长地有感而发:“今后你俩成家后,对我和你娘好不好无所谓,但一定要对公婆好,千万别学有的女人,娘家人就是宝,婆家人就是草。俗话说‘子孝不如媳妇孝,女孝不如女婿孝’。”自小聆听父亲的教诲,我和姐姐跟婆家人的关系都特别好。姐姐和婆婆亲如母女,婆婆和我生活近三年,关系亦很融洽。
父亲常说世上只有瓜连子,哪有子连瓜?可父亲近乎偏执的孝顺,似乎又是子连瓜的典范。晚年的奶奶性情大变,吵闹着要和爷爷分家。最终爷爷和奶奶还是分了家,爷爷归父亲养,奶奶归叔叔养,并各自负责他们的生老病死。因父亲曾强烈反对分家,奶奶一直记恨父亲,她不仅从猫洞里将爷爷的坛坛罐罐戳得破破乱乱,还不时用长竹篙将我们家屋顶的瓦片戳得七零八落,有时奶奶还抱着砧板和菜刀来到我家后山,在砧板上砍一刀骂一句我的父母。后来奶奶摔断了腿,拉屎拉尿全在床上。婶婶见奶奶变为了累赘,先前的甜言蜜语变为爱理不理。父亲见奶奶着实可怜,一辈子没洗过衣服的父亲只好隔三岔五将奶奶沾满屎尿的脏衣服挑到小溪里去洗。
暑假里,父亲时常要我和姐姐去给奶奶送饭,我们见其房间凌乱不堪,就随手帮她收拾了一下,奶奶也许见惯了断腿后的冷眼,竟然对我们感叹道:“你们姐妹俩心肠真好,今后会有好报的。以前对你们家做了好多错事,哎!”大概是鸟之将死,其言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面对形容枯槁行将就木已八十高龄的奶奶,面对曾经诸多疯狂行为给母亲造成严重伤害的奶奶,我们有隐隐的恨,更多的是淡淡的怜。
但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六七十年代,红糖和月饼却是很稀罕的宝物。妈妈生大哥坐月子时仅有的两斤红糖供给量,父亲居然都分了一半给他的父母。有年中秋节父亲从蒙泉水库工地上带回两个月饼,母亲欣喜不已。哪知月饼刚放下不到两分钟,父亲全拿去送给他的父母。气愤至极的母亲和父亲大吵起来:“孝顺父母就不要孩子了?哪怕你只留半个,让大丫头和小丫头各尝一点点,我也没意见,你太绝情了。”父亲却振振有词:“老人吃一天少一天,孩子来日方长,有吃的在后头。”双方各执一词。面对雄辩霸蛮的父亲,善良弱势的母亲泪如决堤的海。同样是爱,没有孰轻孰重,也没有孰是孰非,只不过一个纠结于瓜连子,一个偏执于子连瓜罢了。
家风如春雨,润物细无声。父亲的好学,父亲的孝顺,父亲的豁达,我们从小耳濡目染,铭刻在心,即便是成年后,依然是规范我们自己行为的“调节器”。(丁东珍)